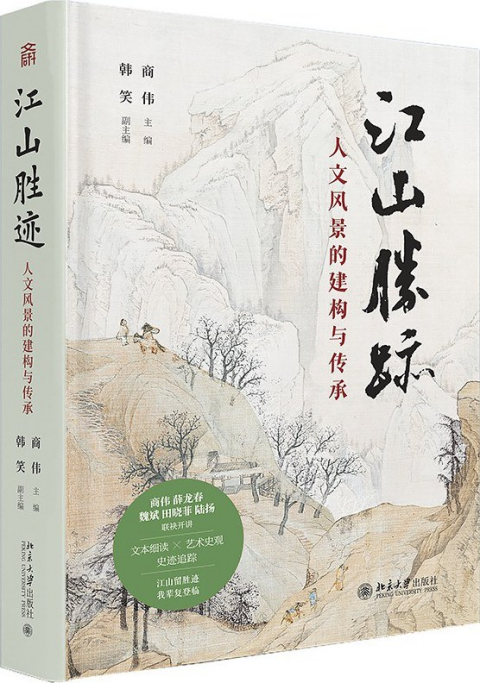《田园山地风景名胜区:人文景观的构建与传承》 主编:【美国人】尚伟韩笑 主编: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5年8月 李白与金陵凤凰楼 关于凤凰楼最早的记载可见于宋代傅睿智的中篇。相传元嘉十四年(437年)三月,莫灵王花园的一棵梅树上,有两只鸟聚集。他们看起来很奇怪。 “其体形如孔雀大小,头足小,羽色鲜艳,文字五色,声音和谐。”扬州彭城王刘义康奏报朝廷,下旨“将百鸟聚集的永昌巷改为凤凰巷”。不过,这里的“嘉修”只提到了“Hoo-ri”,根本没有提到Hoo-Terrace。有趣的是,记载越晚,凤凰楼就越早,这让人想起顾颉刚的《凤凰楼》。的“分层理论”,因此记录可能不可靠。例如,完成于668年的佛教经典《法源书林》,收录了东锦朝(357-361年)《宋书·福瑞氏》中记载的早近80年的吉祥事件,并将“凤历”改为“凤历”。南宋马光祖(约1201-1273年)在其《凤凰丹再造》一文中,也根据淳熙年间(1174-1189年)无聊寺壁画记载,得出“晋级已达阶段”的结论。但他监修的《净定健康志》兼顾了两种说法,含糊其辞:“伯宁禅寺位于城内引虹桥以南的无聊广场。”武帝赤乌四年为西楚康寺(回民)修建,名建中。凤翔长年云集此山。”金宋时期于是,庙旁建了一座凤凰台。建中寺,即后来的无聊寺,元末毁,其遗址并入和观寺。据史料记载,瓦观寺始建于金兴宁二年(364年)。明初寺院废弃,遗址未探。温伯伦的《凤凰台》,上海博物馆藏。 “长山风景区”插图 直到嘉靖时代(1522-1566),兴化村一带才修建了地清庵,并出土了成源(937-943)石像。由于此地被确认为早和石寺遗址,因此更名为兴和石寺,凤凰台遗址也再次得到确认。明代时,凤凰台遗址已传至卫国公的田地里,后来渐渐孤独。 “他们为那些幸存的人建造了一座尼姑庵,旁植桂花,名‘空归’。”从归庵与古瓦观寺相对,后称山瓦观寺。明朝焦弘(1540-1620)提议改名丰佑寺。详见其《重修法玉寺碑记》。清初周梁公 (1612-1672)顺治年间(1644-1661)和康熙六年(1667)开始集资赎地,重建凤凰楼。他又写了《赎回凤凰关请愿书》和《呼吁重建瓦观寺凤凰关》,重申了凤凰关的根基。 凤凰关位于古瓦观寺左侧。康熙初年,贾县宁县长陈开宇曾撰有《凤端诗》,收录于他所编的《建宁县志》《山河图》卷五。诗的序言这样写道:“那个露台是“它被大地猎人们掠夺和破坏了,既然我禁止了它,我就将它恢复原样,让它永垂不朽。”陈开宇对康熙时期的募捐活动赞不绝口。承认了,但是效果并不显着。不久之后,凤凰塔再次消失在沙漠之中,再也无法辨认。金陵李白的《登凤凰阶》是现存第一首记录凤凰阶的诗,正是通过这首诗,后人记住了凤凰阶。值得注意的是,李白还提到了与凤凰楼有关的景点。例如《横江六师》中写到“白廊高于若观亭”,还有一首诗叫“十若观华”。早稻阁位于凤凰台附近,因早稻寺而得名。虽然当时很受游客欢迎,但凤凰台却很少被提及。此外,还有关于凤凰的记载。金陵塔,据梁代高僧惠教所著《名僧传》记载,天竺僧人祈求那瓦陀罗“在秣陵边境凤凰塔西建寺”。这个说法比《诗经》中关于凤凰楼的记载还要古老。后来,唐代徐嵩编着的《六朝宫苑记》中也记载:“凤凰塔位于凤台山,始建于宋嘉中,始建于元代,因凤凰塔而得名。凤凰塔的修建年代可追溯至刘、宋、元、嘉年间。” 如果追溯到很久以前,这与宋代项睿智凤凰聚集于此的记载相符。李白的《邓和官亭》中有这样的诗句:“门关楼内知凤名”,《金陵月夜村》中也有这样的诗句:平台向喜鹊倾斜,宫内无帝凤楼。”原来,凤凰楼已毁已久,仅存其名。李白去世一百多年后,诗人尹耀凡(780-855)在其《两次登凤凰台》一书中写道:“登凤凰台看长安, 五色宫袍倒映在冰冷的水中。彩笔在书法中保留了十年。银河一夜干空。”他还说:“秋风中梧桐叶落,人离台凤凰不来。”在这首诗中,作者不仅重复了李白的“登金陵凤凰楼”,还提到了李白奉旨入朝,却又失意而归。 凤凰台的目的是祭奠和纪念李白。李群玉(约813年 – 约860年),诗人晚唐时期,曾写下《秣陵忆古》诗。古吴宫里野花黄叶盛开,六朝时期的美丽烛光散落在风中。如今,龙虎之力减弱,善灵消失,凤凰的名字,刻在了古台的上空。随着城市从一个王朝到另一个王朝的更迭,秋天变绿,高低坟墓亮起红色。霸主和定土都消失了,只剩下我一个人在阴沉的水云里。与应耀凡不同,李群玉根本没有提到李白和他的“登金陵凤凰楼”。他称凤凰台为“老五宫”,如“老五宫”。美好的氛围消失了,浪漫消散了,成为了前朝的过去。唐朝时期,金陵凤凰塔唱歌并不流行,凤凰ix宝塔并没有成为游客“打卡”的地方。那么当时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呢?古人所说的“台”,原本是与楼观这样的建筑分开的。平台可以是任何高于周围环境的平坦地形,无论是自然形成的、夯土的还是由砖块或石头制成的。 《霍根祖林》中写道:“因凤凰聚集于此,故名凤凰台”。是。凤凰台之名,源于传说中的凤凰曾聚集于此,并无意在此筑台。这个命名方案与李白模仿的沉佺期《龙池表》第一句的含义一致:“龙跃潭,龙飞”。 “龙池”之所以叫“龙池”,只是因为传说中曾经有一条龙来过这里,并不是因为龙来了之后才建的龙池。李白《凤台》“火鸟离去,火鸟离台”“天是天,河独流”,正如其所言。也就是说,李白所游览的凤凰塔不一定是有意建造的,在当时也并不出名。李白是第一个将其写成诗的人。因此,凤凰塔的存在并不取决于凤凰塔的存在,而是凤凰塔的存在取决于诗。与李白的对应关系 白的诗意描述已失传。 poLater的作品有时会提及凤凰塔的高度和规模,但大多数都是虚构的,没有事实根据。例如宋代杨万里的诗云:“凤凰塔高百尺,送潮不复”。 “严格来说,这并非来自对场景的观察或描述,而是来自悠久的文学传统。回顾筑台登台题材的文学作品,兵马俑的由来这可能是《诗经》中周文王关于灵坛、沼泽、灵牢的歌。 ”楚王修筑了许多高台,如陆云《新游》中写道:“楚灵王在千川筑高台五百尺,以登浮云观天象。”“楚王如此,汉王更是如此。他们搭建的高坛与长生不老的理念密切相关。凤凰原本是从天而降的瑞鸟,诗人想象有一座“百尺”高的凤凰坛。宋代吴景波也有诗描述此事。 《秦元春·登凤凰阶》:“再去高台拜仙,仙人在哪里?”他用李白代替了凤凰,将自己流仙的身份融入到了高台寻仙的想法之中。这是因为高平面拜访隐士仅凭形式是不够的。陈左的《凤凰台》。 《凤山胜景》图解 唐宋以后凤凰塔的处境并不重要。王朝、地方官员和地方文人继续尝试重建凤凰塔。至少有三个重大重建项目。但重建后,又年久失修。这要追溯到宋秋秋(887-959)《游凤凰台献诗》(其作品之一为《铭记》《凤台山亭,陈贤四公》)中写的两行诗:“顶上有官台,八楼在城中。” “原来唐宋时期,这里的扶正阁曾被称为凤凰台,因此,凤凰台只是作为人们祭祀的地名。”早在马光祖之前,陆游也曾游览过凤凰台。根据据记载,1169年至1170年间,保宁寺有凤凰台和揽慧阁,但记载“现已废弃为军械库,但阁已在古址上重建,甚为宏伟”。引用林希仪诗《凤凰》序言中的一句话。南宋《秋台》:“凤凰台名于李翰林诗。有趣的是,李翰林参观凤凰台时,却走错了地方。于思翰林作诗时,白鹿舟不可能在露台上。”问起时,老导师指出,没有固定地点,三座山在露台上看不到,位于潜江尽头很远的地方。这首诗如果是当时作的,不应该这样模仿。我已修改出版,以待后人评价。 希仪来到这里,唯一瘦了我想到的就是李白的《登金陵凤凰阶》和《青天出三山半倒一水》。 “分白鹭洲”,眼前的景色却完全格格不入。怎么了?林诗意有可能走错地方了。然而,即使他们去对了地方,也看不到李白诗中所描述的风景。为什么这么说?清代吴敬梓(1701-1754)在《金陵山水诗·凤凰丹》序中解释道:唐代时,嵊州城规模尚小。从这里远眺雄伟的杨行密城墙,南望淮河。五朝十国时期的吴国(902-937),因其创始人为杨行密(852-905),又称杨吴。杨武占领江淮地区,西定金陵。徐文将军重建金陵城,将今内陆秦淮河纳入城内,并在城周围挖护城河,史称阳武城壕。金陵的水系、城市布局和自然景观都发生了变化。对照《唐胜州图》与康熙《建宁府史》中的《南唐江宁府图》可知,凤凰台原本沿河而建,周围有城墙环绕。从此,这一地区的自然景观就失去了与李白诗意描述的对应关系。清道光年间(1821-1850年),周宝钧写了一首《凤凰台》诗。上联和下巴联写着:“凤凰台被夷为平地,还有一些名人尚未消灭。”远处可以看到两条河,但在城市的高处也可以看到三座山,对吗?序言中写道:“(尼克丹)曾经毗邻河流,后来被杨武筑城所覆盖,三山和白鹭州都已看不见了。”杨武之后,这里的地理形态也逐渐发生了变化。由于凤凰台位于河流一角,与河岸相连,而长期的沉积对白鹭洲的河面造成了压力。因此, 长江远离凤凰台。周宝军在世时,昔日的“白鹭岛分为水两部分”的地貌已经完全改变。此外,日益密集的住宅建筑和商业活动加剧了自然环境的恶化。高耸的城墙遮挡了江景,无法恢复“三山半蓝天”的深邃景色。什么是 有趣的是,凤凰塔碑刻的流行正是在唐南宋之后,之后金陵城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当然,地理环境难免会改变,但写诗还是可以的。然而,真正令人惊讶的是,这些诗几乎没有揭示当时凤凰楼的景观。有的诗人也时不时感叹野树太多,古迹荡然无存。忘记必须避免的是,凤凰梯田遗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被调查了。然而,大部分碑文作者却仿佛还活在李白笔下的凤凰台文字景观中,仿佛一切的变迁从未发生过。或者,让我们想象一下,凤凰一如往常地矗立在江边的广阔景观,正如宋代郭象正(1035-1113)的诗中所说:“高台上无凤凰游,雄伟的长江入海。”凤凰台风景,明代焦洪的诗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:“望东南,长空有雁”。对此,我们应该多么感谢林希仪、周宝轩这样的诗人啊!因为他们揭示了凤凰塔纪念碑的真相和现实,所以我们并没有被蒙在鼓里。重新确认的凤凰台遗址已经发生了变化。了解真相只是问题的开始。宋代以后的诗人虽然继续写金陵凤凰丹,但很少写现在的山水。是因为我“厌倦了露台上的风景”而无事可写吗?当我无事可写时,为什么还要继续写?答案可以很复杂也可以很简单。这些诗人之所以来到这里,是因为他们相信李白曾经来过这里。金陵凤凰台因李白曾到此而具有独特的意义。更重要的是,李白留下了《登金陵凤凰阶》。他们根据李白的诗写了《凤凰台》诗歌而不是他们面前的场景,因此身体存在并不是必要的先决条件。这个高度文本化的凤凰台取代了实体的凤凰台,成为了凤凰台文字永恒的滋生地。此后,不断有新的作品诞生,李白亲自在凤步上题字纪念。这就是宇文所安所说的,碑终于成为碑,激励历代诗人继续书写。后人通过不断的书写,加入史迹的文字谱系,从纪念者转变为纪念者。 《金陵四十八景》和《凤凰山关三》,形似长钱。 《凤山风景区》图解补充一下,随着时间的推移,重新确认的凤凰台的位置也发生了很多变化。例如,旁边发现了“阮籍墓”明万历年间的凤凰台。清人周宝钧的《凤凰台》最后两句是这样的:酒幕邀客争,笛牛群回记忆。我含着热泪前来吊唁,因为有人告诉我,唯一剩下的石碑将献给真陵。诗序云:“(凤凰台)在今小七仓西南,旁有金代恩官君墓。”据康熙治《建宁县志》(陈开宇主修)蒋欧岳所著《清初凤凰级改造与文化复兴》一文记载,阮籍墓的记载首次见于姚禄(约1977年)《庐书》卷七“遗迹”篇。 1572-?)明朝。 ”:“秣陵凤凰台旁,是阮籍墓。李公昭在任城发掘石碑的一半,称为“池墓”,另一半,称为“进贤阮”。后来得知,这里就是阮基的坟墓。后来有些人变得贫穷并做出了很多牺牲。季氏的踪迹主要发现于山阳,但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被埋在这里。 ”此事发生在万历任城,即公元1592年。周亮所著《赎凤台集》,抄录了姚笠的话,但“三阳多有其居住痕迹,但不知其为何葬于此”一句已被删去。他还引用了刘廷录《凤凰台诗》中的两句。 金陵:“阮姬墓什么时候到?金陵必有坟。”他坚称“一切都清楚了,有据可查。”吴世子在《金陵山水诗序》中对这种描述有些怀疑,说有人怀疑这是阮孝胥的坟墓。他认为阮氏祖屋就是陈六味家族。阮氏死于魏朝。他不是晋人,不应该葬在吴国。然而,由于阮孝胥(479-536)不是金朝人,金陵的理论并不成立。但瞻仰墓地最终成为游览凤凰台的一个特殊部分。在凤阶上刻字的人有时会写“暖步兵墓”或“晋墓”,如吴敬梓、周宝春等。有趣的是,阮籍和阮孝绪都不是金代人,虽然无法证明这是一座金墓,但人们仍在寻找它。堪比金代墓葬。清初陈开宇编着的《建宁县志》中记载:“关白库诗‘晋衣冠成古山’,绝指阮墓。”表面上,陈开宇在李白的诗中找到了墓主身份的证据,并用了“p”一词。事实上,他通过确认墓主人的身份,“完成”了李白的作品,从而在“晋衣成古山”的景观中解读了这座明代发现的古墓。明代沈世充的《南京十景》和《江山胜景》插画。 仔细阅读上述著作,并讨论史料,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:作为凤凰楼文本化的开山之作,《李白登金陵凤凰楼》不仅是关于金陵凤凰楼的,而且超越了这个独特的地点。李白的诗中当然有关于三山、白鹭洲的诗,构成了三山、白鹭洲不可替代的特殊性。 凤凰丹山水,但他也将凤凰丹山水纳入了更为普遍的文本模式。前往凤凰台的游客,请输入由这种诗意的语言意味着离开当前所处的地理空间,通过现在与过去、名与实、存在与虚无、看见与看不见等一系列时态对比的短语来重构与风景地点的关系,完成凤凰台的视觉体验。事实上,一旦诗歌的语言模式内化为灵魂的感性结构,人们就能在此时此地强烈地感受到“短暂与永恒、毁灭与生存、消失与可见之间的张力”,这是汉斯·H·弗兰克尔对程江五字古诗《仙山乡愁》的评论,也概括了历史书写的基本方式。 网站,尤其是怀旧诗歌。这说明李白的凤凰丹作品具有普遍性,其存在不依赖于特定地点。它代表了一种景观精神及其实习生铝结构。这种精神景观起源于诗意语言的形成,因此在任何特定的旅游观察或体验发生之前就存在。它是内部化的,可以存储和传输,并且可以随时从读取存储器中检索。它通过外部机会投射到访问者当前的位置,并且这个特定位置可以与与之相关的记录和谣言进行交互。凤凰台的面貌已经弯曲,景观被彻底破坏,遗址也没有同时通过检查,都不尽如人意。但历史记载的措辞依然如故,不会因此而停止或停止。这种“凤凰楼现象”看似特殊、矛盾,但却揭示了历史书写背后的一个重要前提。也就是说,一座高度文字化的凤凰塔,将会比实体的凤凰塔更加坚固,更加持久。这是李白那些关于凤凰台的诗歌,而不是凤凰台本身,激活并维持了凤凰台的文化记忆,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,并通过写作将其永存。本文节选自《风景名胜:人文景观的建构与传承》。本文使用的所有插图均取自本书。经出版商许可出版。原作者/尚伟,摘录韩晓/何编辑/张晋/赵琳简介审稿
《田园山地风景名胜区:人文景观的构建与传承》 主编:【美国人】尚伟韩笑 主编: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5年8月 李白与金陵凤凰楼 关于凤凰楼最早的记载可见于宋代傅睿智的中篇。相传元嘉十四年(437年)三月,莫灵王花园的一棵梅树上,有两只鸟聚集。他们看起来很奇怪。 “其体形如孔雀大小,头足小,羽色鲜艳,文字五色,声音和谐。”扬州彭城王刘义康奏报朝廷,下旨“将百鸟聚集的永昌巷改为凤凰巷”。不过,这里的“嘉修”只提到了“Hoo-ri”,根本没有提到Hoo-Terrace。有趣的是,记载越晚,凤凰楼就越早,这让人想起顾颉刚的《凤凰楼》。的“分层理论”,因此记录可能不可靠。例如,完成于668年的佛教经典《法源书林》,收录了东锦朝(357-361年)《宋书·福瑞氏》中记载的早近80年的吉祥事件,并将“凤历”改为“凤历”。南宋马光祖(约1201-1273年)在其《凤凰丹再造》一文中,也根据淳熙年间(1174-1189年)无聊寺壁画记载,得出“晋级已达阶段”的结论。但他监修的《净定健康志》兼顾了两种说法,含糊其辞:“伯宁禅寺位于城内引虹桥以南的无聊广场。”武帝赤乌四年为西楚康寺(回民)修建,名建中。凤翔长年云集此山。”金宋时期于是,庙旁建了一座凤凰台。建中寺,即后来的无聊寺,元末毁,其遗址并入和观寺。据史料记载,瓦观寺始建于金兴宁二年(364年)。明初寺院废弃,遗址未探。温伯伦的《凤凰台》,上海博物馆藏。 “长山风景区”插图 直到嘉靖时代(1522-1566),兴化村一带才修建了地清庵,并出土了成源(937-943)石像。由于此地被确认为早和石寺遗址,因此更名为兴和石寺,凤凰台遗址也再次得到确认。明代时,凤凰台遗址已传至卫国公的田地里,后来渐渐孤独。 “他们为那些幸存的人建造了一座尼姑庵,旁植桂花,名‘空归’。”从归庵与古瓦观寺相对,后称山瓦观寺。明朝焦弘(1540-1620)提议改名丰佑寺。详见其《重修法玉寺碑记》。清初周梁公 (1612-1672)顺治年间(1644-1661)和康熙六年(1667)开始集资赎地,重建凤凰楼。他又写了《赎回凤凰关请愿书》和《呼吁重建瓦观寺凤凰关》,重申了凤凰关的根基。 凤凰关位于古瓦观寺左侧。康熙初年,贾县宁县长陈开宇曾撰有《凤端诗》,收录于他所编的《建宁县志》《山河图》卷五。诗的序言这样写道:“那个露台是“它被大地猎人们掠夺和破坏了,既然我禁止了它,我就将它恢复原样,让它永垂不朽。”陈开宇对康熙时期的募捐活动赞不绝口。承认了,但是效果并不显着。不久之后,凤凰塔再次消失在沙漠之中,再也无法辨认。金陵李白的《登凤凰阶》是现存第一首记录凤凰阶的诗,正是通过这首诗,后人记住了凤凰阶。值得注意的是,李白还提到了与凤凰楼有关的景点。例如《横江六师》中写到“白廊高于若观亭”,还有一首诗叫“十若观华”。早稻阁位于凤凰台附近,因早稻寺而得名。虽然当时很受游客欢迎,但凤凰台却很少被提及。此外,还有关于凤凰的记载。金陵塔,据梁代高僧惠教所著《名僧传》记载,天竺僧人祈求那瓦陀罗“在秣陵边境凤凰塔西建寺”。这个说法比《诗经》中关于凤凰楼的记载还要古老。后来,唐代徐嵩编着的《六朝宫苑记》中也记载:“凤凰塔位于凤台山,始建于宋嘉中,始建于元代,因凤凰塔而得名。凤凰塔的修建年代可追溯至刘、宋、元、嘉年间。” 如果追溯到很久以前,这与宋代项睿智凤凰聚集于此的记载相符。李白的《邓和官亭》中有这样的诗句:“门关楼内知凤名”,《金陵月夜村》中也有这样的诗句:平台向喜鹊倾斜,宫内无帝凤楼。”原来,凤凰楼已毁已久,仅存其名。李白去世一百多年后,诗人尹耀凡(780-855)在其《两次登凤凰台》一书中写道:“登凤凰台看长安, 五色宫袍倒映在冰冷的水中。彩笔在书法中保留了十年。银河一夜干空。”他还说:“秋风中梧桐叶落,人离台凤凰不来。”在这首诗中,作者不仅重复了李白的“登金陵凤凰楼”,还提到了李白奉旨入朝,却又失意而归。 凤凰台的目的是祭奠和纪念李白。李群玉(约813年 – 约860年),诗人晚唐时期,曾写下《秣陵忆古》诗。古吴宫里野花黄叶盛开,六朝时期的美丽烛光散落在风中。如今,龙虎之力减弱,善灵消失,凤凰的名字,刻在了古台的上空。随着城市从一个王朝到另一个王朝的更迭,秋天变绿,高低坟墓亮起红色。霸主和定土都消失了,只剩下我一个人在阴沉的水云里。与应耀凡不同,李群玉根本没有提到李白和他的“登金陵凤凰楼”。他称凤凰台为“老五宫”,如“老五宫”。美好的氛围消失了,浪漫消散了,成为了前朝的过去。唐朝时期,金陵凤凰塔唱歌并不流行,凤凰ix宝塔并没有成为游客“打卡”的地方。那么当时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呢?古人所说的“台”,原本是与楼观这样的建筑分开的。平台可以是任何高于周围环境的平坦地形,无论是自然形成的、夯土的还是由砖块或石头制成的。 《霍根祖林》中写道:“因凤凰聚集于此,故名凤凰台”。是。凤凰台之名,源于传说中的凤凰曾聚集于此,并无意在此筑台。这个命名方案与李白模仿的沉佺期《龙池表》第一句的含义一致:“龙跃潭,龙飞”。 “龙池”之所以叫“龙池”,只是因为传说中曾经有一条龙来过这里,并不是因为龙来了之后才建的龙池。李白《凤台》“火鸟离去,火鸟离台”“天是天,河独流”,正如其所言。也就是说,李白所游览的凤凰塔不一定是有意建造的,在当时也并不出名。李白是第一个将其写成诗的人。因此,凤凰塔的存在并不取决于凤凰塔的存在,而是凤凰塔的存在取决于诗。与李白的对应关系 白的诗意描述已失传。 poLater的作品有时会提及凤凰塔的高度和规模,但大多数都是虚构的,没有事实根据。例如宋代杨万里的诗云:“凤凰塔高百尺,送潮不复”。 “严格来说,这并非来自对场景的观察或描述,而是来自悠久的文学传统。回顾筑台登台题材的文学作品,兵马俑的由来这可能是《诗经》中周文王关于灵坛、沼泽、灵牢的歌。 ”楚王修筑了许多高台,如陆云《新游》中写道:“楚灵王在千川筑高台五百尺,以登浮云观天象。”“楚王如此,汉王更是如此。他们搭建的高坛与长生不老的理念密切相关。凤凰原本是从天而降的瑞鸟,诗人想象有一座“百尺”高的凤凰坛。宋代吴景波也有诗描述此事。 《秦元春·登凤凰阶》:“再去高台拜仙,仙人在哪里?”他用李白代替了凤凰,将自己流仙的身份融入到了高台寻仙的想法之中。这是因为高平面拜访隐士仅凭形式是不够的。陈左的《凤凰台》。 《凤山胜景》图解 唐宋以后凤凰塔的处境并不重要。王朝、地方官员和地方文人继续尝试重建凤凰塔。至少有三个重大重建项目。但重建后,又年久失修。这要追溯到宋秋秋(887-959)《游凤凰台献诗》(其作品之一为《铭记》《凤台山亭,陈贤四公》)中写的两行诗:“顶上有官台,八楼在城中。” “原来唐宋时期,这里的扶正阁曾被称为凤凰台,因此,凤凰台只是作为人们祭祀的地名。”早在马光祖之前,陆游也曾游览过凤凰台。根据据记载,1169年至1170年间,保宁寺有凤凰台和揽慧阁,但记载“现已废弃为军械库,但阁已在古址上重建,甚为宏伟”。引用林希仪诗《凤凰》序言中的一句话。南宋《秋台》:“凤凰台名于李翰林诗。有趣的是,李翰林参观凤凰台时,却走错了地方。于思翰林作诗时,白鹿舟不可能在露台上。”问起时,老导师指出,没有固定地点,三座山在露台上看不到,位于潜江尽头很远的地方。这首诗如果是当时作的,不应该这样模仿。我已修改出版,以待后人评价。 希仪来到这里,唯一瘦了我想到的就是李白的《登金陵凤凰阶》和《青天出三山半倒一水》。 “分白鹭洲”,眼前的景色却完全格格不入。怎么了?林诗意有可能走错地方了。然而,即使他们去对了地方,也看不到李白诗中所描述的风景。为什么这么说?清代吴敬梓(1701-1754)在《金陵山水诗·凤凰丹》序中解释道:唐代时,嵊州城规模尚小。从这里远眺雄伟的杨行密城墙,南望淮河。五朝十国时期的吴国(902-937),因其创始人为杨行密(852-905),又称杨吴。杨武占领江淮地区,西定金陵。徐文将军重建金陵城,将今内陆秦淮河纳入城内,并在城周围挖护城河,史称阳武城壕。金陵的水系、城市布局和自然景观都发生了变化。对照《唐胜州图》与康熙《建宁府史》中的《南唐江宁府图》可知,凤凰台原本沿河而建,周围有城墙环绕。从此,这一地区的自然景观就失去了与李白诗意描述的对应关系。清道光年间(1821-1850年),周宝钧写了一首《凤凰台》诗。上联和下巴联写着:“凤凰台被夷为平地,还有一些名人尚未消灭。”远处可以看到两条河,但在城市的高处也可以看到三座山,对吗?序言中写道:“(尼克丹)曾经毗邻河流,后来被杨武筑城所覆盖,三山和白鹭州都已看不见了。”杨武之后,这里的地理形态也逐渐发生了变化。由于凤凰台位于河流一角,与河岸相连,而长期的沉积对白鹭洲的河面造成了压力。因此, 长江远离凤凰台。周宝军在世时,昔日的“白鹭岛分为水两部分”的地貌已经完全改变。此外,日益密集的住宅建筑和商业活动加剧了自然环境的恶化。高耸的城墙遮挡了江景,无法恢复“三山半蓝天”的深邃景色。什么是 有趣的是,凤凰塔碑刻的流行正是在唐南宋之后,之后金陵城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当然,地理环境难免会改变,但写诗还是可以的。然而,真正令人惊讶的是,这些诗几乎没有揭示当时凤凰楼的景观。有的诗人也时不时感叹野树太多,古迹荡然无存。忘记必须避免的是,凤凰梯田遗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被调查了。然而,大部分碑文作者却仿佛还活在李白笔下的凤凰台文字景观中,仿佛一切的变迁从未发生过。或者,让我们想象一下,凤凰一如往常地矗立在江边的广阔景观,正如宋代郭象正(1035-1113)的诗中所说:“高台上无凤凰游,雄伟的长江入海。”凤凰台风景,明代焦洪的诗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:“望东南,长空有雁”。对此,我们应该多么感谢林希仪、周宝轩这样的诗人啊!因为他们揭示了凤凰塔纪念碑的真相和现实,所以我们并没有被蒙在鼓里。重新确认的凤凰台遗址已经发生了变化。了解真相只是问题的开始。宋代以后的诗人虽然继续写金陵凤凰丹,但很少写现在的山水。是因为我“厌倦了露台上的风景”而无事可写吗?当我无事可写时,为什么还要继续写?答案可以很复杂也可以很简单。这些诗人之所以来到这里,是因为他们相信李白曾经来过这里。金陵凤凰台因李白曾到此而具有独特的意义。更重要的是,李白留下了《登金陵凤凰阶》。他们根据李白的诗写了《凤凰台》诗歌而不是他们面前的场景,因此身体存在并不是必要的先决条件。这个高度文本化的凤凰台取代了实体的凤凰台,成为了凤凰台文字永恒的滋生地。此后,不断有新的作品诞生,李白亲自在凤步上题字纪念。这就是宇文所安所说的,碑终于成为碑,激励历代诗人继续书写。后人通过不断的书写,加入史迹的文字谱系,从纪念者转变为纪念者。 《金陵四十八景》和《凤凰山关三》,形似长钱。 《凤山风景区》图解补充一下,随着时间的推移,重新确认的凤凰台的位置也发生了很多变化。例如,旁边发现了“阮籍墓”明万历年间的凤凰台。清人周宝钧的《凤凰台》最后两句是这样的:酒幕邀客争,笛牛群回记忆。我含着热泪前来吊唁,因为有人告诉我,唯一剩下的石碑将献给真陵。诗序云:“(凤凰台)在今小七仓西南,旁有金代恩官君墓。”据康熙治《建宁县志》(陈开宇主修)蒋欧岳所著《清初凤凰级改造与文化复兴》一文记载,阮籍墓的记载首次见于姚禄(约1977年)《庐书》卷七“遗迹”篇。 1572-?)明朝。 ”:“秣陵凤凰台旁,是阮籍墓。李公昭在任城发掘石碑的一半,称为“池墓”,另一半,称为“进贤阮”。后来得知,这里就是阮基的坟墓。后来有些人变得贫穷并做出了很多牺牲。季氏的踪迹主要发现于山阳,但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被埋在这里。 ”此事发生在万历任城,即公元1592年。周亮所著《赎凤台集》,抄录了姚笠的话,但“三阳多有其居住痕迹,但不知其为何葬于此”一句已被删去。他还引用了刘廷录《凤凰台诗》中的两句。 金陵:“阮姬墓什么时候到?金陵必有坟。”他坚称“一切都清楚了,有据可查。”吴世子在《金陵山水诗序》中对这种描述有些怀疑,说有人怀疑这是阮孝胥的坟墓。他认为阮氏祖屋就是陈六味家族。阮氏死于魏朝。他不是晋人,不应该葬在吴国。然而,由于阮孝胥(479-536)不是金朝人,金陵的理论并不成立。但瞻仰墓地最终成为游览凤凰台的一个特殊部分。在凤阶上刻字的人有时会写“暖步兵墓”或“晋墓”,如吴敬梓、周宝春等。有趣的是,阮籍和阮孝绪都不是金代人,虽然无法证明这是一座金墓,但人们仍在寻找它。堪比金代墓葬。清初陈开宇编着的《建宁县志》中记载:“关白库诗‘晋衣冠成古山’,绝指阮墓。”表面上,陈开宇在李白的诗中找到了墓主身份的证据,并用了“p”一词。事实上,他通过确认墓主人的身份,“完成”了李白的作品,从而在“晋衣成古山”的景观中解读了这座明代发现的古墓。明代沈世充的《南京十景》和《江山胜景》插画。 仔细阅读上述著作,并讨论史料,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:作为凤凰楼文本化的开山之作,《李白登金陵凤凰楼》不仅是关于金陵凤凰楼的,而且超越了这个独特的地点。李白的诗中当然有关于三山、白鹭洲的诗,构成了三山、白鹭洲不可替代的特殊性。 凤凰丹山水,但他也将凤凰丹山水纳入了更为普遍的文本模式。前往凤凰台的游客,请输入由这种诗意的语言意味着离开当前所处的地理空间,通过现在与过去、名与实、存在与虚无、看见与看不见等一系列时态对比的短语来重构与风景地点的关系,完成凤凰台的视觉体验。事实上,一旦诗歌的语言模式内化为灵魂的感性结构,人们就能在此时此地强烈地感受到“短暂与永恒、毁灭与生存、消失与可见之间的张力”,这是汉斯·H·弗兰克尔对程江五字古诗《仙山乡愁》的评论,也概括了历史书写的基本方式。 网站,尤其是怀旧诗歌。这说明李白的凤凰丹作品具有普遍性,其存在不依赖于特定地点。它代表了一种景观精神及其实习生铝结构。这种精神景观起源于诗意语言的形成,因此在任何特定的旅游观察或体验发生之前就存在。它是内部化的,可以存储和传输,并且可以随时从读取存储器中检索。它通过外部机会投射到访问者当前的位置,并且这个特定位置可以与与之相关的记录和谣言进行交互。凤凰台的面貌已经弯曲,景观被彻底破坏,遗址也没有同时通过检查,都不尽如人意。但历史记载的措辞依然如故,不会因此而停止或停止。这种“凤凰楼现象”看似特殊、矛盾,但却揭示了历史书写背后的一个重要前提。也就是说,一座高度文字化的凤凰塔,将会比实体的凤凰塔更加坚固,更加持久。这是李白那些关于凤凰台的诗歌,而不是凤凰台本身,激活并维持了凤凰台的文化记忆,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,并通过写作将其永存。本文节选自《风景名胜:人文景观的建构与传承》。本文使用的所有插图均取自本书。经出版商许可出版。原作者/尚伟,摘录韩晓/何编辑/张晋/赵琳简介审稿